


2024年11月18日《聊城晚报》2版
婚礼
订婚时商定结婚的“黄道吉日”之后,两家就开始了美好的憧憬,特别是小伙子和姑娘天天盯着日历牌、掰着手指头,期待着这一天早点到来。一年四季都有结婚的,在农村冬天结婚的居多。二十多年前,农村男方接亲一般是六辆自行车组成的车队,后来慢慢地演变为六辆摩托车,没过一两年,又变成了六辆汽车,如今在农村,六辆汽车或租或借,都很方便。
女方收了彩礼也不是白收的,要精心准备很多嫁妆,包括八仙桌、饭桌、衣柜、衣橱、梳妆台(镜子上面有一对燕子)、热水壶、洗脸盆(红色盆沿内有荷花鲤鱼图案)、毛巾等,被褥要“四铺四盖”,被面颜色各不相同,底色有红绿紫,多数是纯色的,也有配各种喜庆图案的。生活富裕之后,嫁妆又陆续增加了自行车、缝纫机、电视机、音响,再后来又有了陪嫁汽车的,多数是十万元以内的汽车。
出嫁当天的早晨,女方家早早准备好酒菜,请抬嫁妆的十几个人以及六个送亲的姑娘吃。酒足饭饱之后,抬嫁妆的队伍先出发,十几个人排成一长队,浩浩荡荡。嫁妆队到了男方家,一般在上午九点前,接亲的队伍和新娘才开始出发,女方家提前安排的六个年龄相当的姑娘作为伴娘一路护送。菏泽单县很多地方有哭嫁的习俗,出门前母女抱着哭,声音很响亮,生离死别一般,一方面风俗里新娘哭得越厉害说明越有孝心,没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,结婚后福气越多;另一方面离开生养自己的父母也确实有些难过,对父母来说,嫁闺女更是件令人难过的事。在我离开家乡上大学及工作之前,多次见过村里嫁姑娘的,都哭。长大后才知这种哭有真哭和假哭之分。娘哭:“我的乖乖,你走了以后娘可怎么过呀!”女儿则拖着长腔哭:“我的娘哎——以后谁来管我呀!”其实心里很明白,以后有自己的男人管,说不定管得更好。当娘的真哭的成分更多一些——辛辛苦苦把女儿拉扯了二十年,突然间成了人家的人,从此以后一年见不了三五回,还不知女婿待女儿好不好。当女儿的则假哭的成分多一些,早就想出嫁去过幸福的生活,尽管有时候这种幸福是想象出来的。不管真哭假哭,声音都很高,眼泪也哗哗地往下流,这是女人的优势。两人哭了一阵,眼看临近中午,就有邻居几个妇女上前劝说安慰,说找了个好女婿,离家又近,是喜事,别哭坏了身子。当娘的趁机刹车不再哭,后来听她说其实早就哭累不想哭了,就等着别人劝呢。姑娘则越劝越哭,一直到上了接亲的自行车还哭哭啼啼。刚一出村,马上用小手绢抹眼,掏出小镜子照一照,一张脸马上变成艳阳天。三天后回娘家,一脸幸福,浑身喜气,见到她娘和邻居笑声不断。
考验新媳妇的第一关是“闹喜”,“越闹越喜”。如果谁家娶媳妇没人闹,冷冷清清的,说明邻里关系没处理好,反而显得很没面子,男方家往往事先安排几个人带头“闹喜”。单县把“闹喜”叫“乱花媳妇”,从新媳妇进村之前就开始了。离新郎的村庄还有半里路,接亲的人就开始燃放鞭炮,告诉村里人新媳妇驾到!村里得到消息,十几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、十来岁的中小学生都急着往村边赶,连刚会跑还不知道媳妇是什么意思的小孩也跟在后面凑热闹。既然叫“乱”,就没有什么章法,有把新娘拉下车的,有往新娘身上扔东西的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扔楝子树结的果实“楝子豆子”,椭圆形,褐色,果实很实在,砸在身上没大碍,砸到脸上则火辣辣地疼。“乱花媳妇”的人对着新娘子来一阵“楝子豆雨”,伴娘在旁边作掩护,也挨了不少砸。两人用胳膊挡着脸往村里跑,但“闹喜”的人比一个连还多,过了这一排,还有下一排。我上小学时,一天中午放学,邻村的新娘刚好从学校门口经过,全校的学生都加入了“乱花媳妇”的行列,有的男学生激动得把课本、作业本、铅笔盒、书包都扔了过去。新娘被砸得直哭,看看离婆家还有近一里路,终于忍不住抢了辆自行车往回逃,把迎亲的吓了一跳,赶紧追了回来,组成一道人墙,护送着新娘才到了新郎家。
到了新郎家,先举行结婚典礼。大家都静下来,农村人最讲规矩,不该乱的时候绝对不乱。主持婚礼的司仪一般是本村德高望重的人,多数时候是村党支部书记,整个婚礼过程非常庄重,不能开玩笑,在司仪主持下,小两口“一拜天地”“二拜高堂”“夫妻对拜”,这个过程只有几分钟。司仪最后宣布:“鸣炮奏乐,‘闹喜’开始!” 鞭炮还没开始响,一帮年轻人就冲上去,把新郎和新娘拥在了一起,新郎的家人为了减轻新娘的压力,往人群中撒喜糖和硬币。“糖衣炮弹”果然管用,一部分人把目标转向地上的喜钱和喜糖。新郎趁机跑了出来,“闹喜”的人也不再理他,反正天天见没什么好乱的。新娘不能往外跑,只能跑进新房内坐在床沿上。“闹喜”的人都围着新娘闹,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,让新娘点烟,故意让她点不着,新娘只好一遍一遍地点。
工作后,我参加城里的婚礼更多,感觉司仪设置的多数程序既不严肃,又让新郎新娘很难受。比如最常见的是,司仪让新郎当着上百客人的面吻新娘,客人们可能会觉得好玩,没有考虑到这会让双方的家长有一些尴尬。再比如司仪提一些类似“结婚后谁做饭、谁管钱”的问题让新郎新娘回答,貌似幽默,实则无趣。最让人难堪的是在婚礼上当众改口、给改口费,司仪让新娘喊婆婆公公“妈”“爸”,往往再加一句:“声音太小没听清楚”,新娘只好再喊一遍,司仪问公公婆婆“满意吗?”回答当然是满意,接着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给儿媳妇。司仪再让新郎喊岳母岳父“妈妈爸爸”,再加一句“听着不够亲,再叫一遍”,问岳父岳母“满意吗?”回答当然也是满意,接着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给女婿。即使新郎新娘都有爱屋及乌之心,都有当演员的基本素质,在尚未与对方父母培养出深厚感情之前,当众叫爸爸妈妈,实在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对双方老人来说,配合演戏也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。
2022年10月2日,我高中同学瑞兵和爱华的儿子朱琳结婚,瑞兵让我当证婚人,我是看着朱琳从小长大的,很愉快地答应了,带着母亲和全家人都去了菏泽。婚礼上第一次遇到没有改口和给改口费这个程序,也没有问婚后谁管钱谁做饭的问题,不由得对司仪肃然起敬。我想既然司仪这么不落俗套,我也不能按老套路读结婚证了,临时决定对喜公公(瑞兵)和喜婆婆(爱华)讲两点,对新郎新娘讲三点。跟瑞兵和爱华讲的两点:一是上初中时我和瑞兵挤一张床睡觉,我嫌他的脚臭但我从来没有说过,瑞兵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;二是告诉爱华要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——在她和瑞兵同床共枕之前的六年,我就和瑞兵同过床了。我跟新郎新娘讲的三点是:一是要感谢我们的党和国家,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,就没有你们今天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,就不可能在这么高级的酒店举办婚礼、吃好菜喝好酒。二是要感谢双方的父母特别是对方的父母,没有父母的辛苦培养,就没有出色的你们,你们也遇不到优秀的对方。三是要感谢对方,人无完人,但在对方眼里你是完美的,也只有在对方眼里你才是完美的。跟新郎新娘讲的第一点还没有讲完,全场掌声雷动。第二天,朱琳把他同学群的对话截屏发给我,都对我讲的第一点认可加佩服,说明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那么难做,只要说话有情有理有据,就能入耳入脑入心。回家后母亲问我:“你讲话时是不是紧张了?别人都笑,你一直没有笑。”我说:“您看看那些说相声的,有几个自己笑的?”
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也是非常重要的,是吃大桌。对绝大多数参加婚礼的亲友来说,整个结婚程序最吸引人的不是新娘子漂不漂亮,而是吃大桌,也有叫吃大席的。小孩们包括一部分成年人去参加亲戚家的婚礼,注意力主要在菜上,往往吃完大桌回家时,连新娘子什么模样都不清楚。
每个村都有两三个专门为红白事做大席的,单县叫“焗匠”,周边县也有叫“焗人”的,“人”显然没有“匠”更有水平。我舅是他村里的焗匠,几乎每个月都要做一两次,焗匠都是免费做饭,报酬是跟着吃两顿饭喝点酒,外加两盒烟。每年正月初二或者正月初三我全家去看姥娘和舅,都是舅负责做菜,非常好吃。我至今没有吃过比他做得更好吃的菜。我一个表叔在孙六镇上开饭店,也承做婚宴,味道很好,特别是做的麻辣乳羊是一绝,味美价廉,很多县城里的人开车去吃。从二十年前我就多次动员舅和表叔到济南开个饭店,赚的钱绝对是在孙六的好几倍,舅因为家里人多事多离不开他,表叔则小富即安故土难离,终究没有圆我常吃大桌的心愿。
说是吃大桌,其实桌子并不大,是从邻居各家借来的切菜和面的案板。板凳不够用,就搬几块砖坐。盘子、碗、筷子、蒸笼有专门出租的。送新媳妇的和抬嫁妆的娘家人在屋里吃,标准高一些,其他的亲朋好友都在院子里吃,村里每家来一个人吃大桌。一般在自家院子里摆十几桌,借邻居院子摆十几桌,有的家庭直接在家门口的路上摆长长的几十桌。赶上下雨天,有提前做准备的就搭起一个个帆布棚,来不及准备帆布的,就淋着雨吃,场面极为壮观。最浪漫的是赶上下雪天,北风萧萧,雪花飘飘,飞舞在桌子上及亲友们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。男人坐一起,妇女坐一起,小孩坐一起。凉菜端上来,还没有来得及结冰就被吃完了,热菜端上来还没有变凉就被吃光了。本家族的人和帮忙做饭的“忙客”,要等亲戚朋友吃完后才能吃。
先上喝酒的小菜,叫酒肴,多为凉菜和素菜。男人们喝酒,妇女和小孩喝水,以水代酒。大人们吃得较文雅,抿口酒,夹口菜,放下筷子,唠几句家常。再喝口酒,夹口菜,再放下筷子,说说话。小孩桌上不喝酒,却更热闹。尽管临来之前家长们有交代:少吃酒肴,鸡鱼肉都在后面,吃多了酒肴,后面的好菜就吃不下了。但多数小孩耐不住性子等后面的“好戏”,不喝酒,也不故作斯文,一盘菜上来,八九双筷子长驱直入,不甘示弱,在盘中你来我往,战作一团。扫光一盘,用筷子敲着空盘子瞅着大人桌上的菜等下盘菜。再上一盘,激烈场面重演。吃饭的菜上来,一般是十个大菜,有的用十个大盘子,也有用十个大碗的。鸡鱼肉等热菜是头天晚上做好的,放在笼里蒸一蒸就可以端上来,上菜的速度很快。人在盘中碰筷子,狗在桌下抢骨头,把桌子顶得悠悠颤动。一条高大健壮的狗见桌子太矮,蜷着身子趴在桌下,津津有味地边吃骨头边摇尾巴,尾巴尖扫到一个小孩脸上,小孩猛踹还击,大狗受惊猛起,顶着桌子就往院外跑,桌上的盘子掉到地上,连菜带汤撒了一地,几条小狗兴冲冲地跑过来抢,将本来很平的地面舔出了几道沟。
我上初一时,一位表哥结婚。头天晚上,母亲对我说:“明天你表哥娶新媳妇,咱们全家都去吃大桌,你给老师请个假。”我那时是个比较自律的好学生,感冒发烧都没请过假,怎么好意思为了吃大桌请假?望子成龙的母亲也不想让我耽误功课,但还是不想让我错过一次吃大桌的难得机会,跟我说:“你表哥结婚咱家交的喜礼多,去的人少吃不够本。”终于做通了我的工作。第二天上午上完三节课后,我战战兢兢地去找班主任马继坡老师请假,我说:“马老师,我想请一节课的假。”马老师关切地问我:“是不是病了?”我说:“没病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要请假?”我开始害怕和后悔起来,说:“我不请假了。”马老师奇怪地问:“有什么事就直说,没关系。”我脑子里又闪现出大桌上的肉和菜,鼓了鼓勇气说:“我表哥今天结婚。”马老师听了两眼笑成一道缝:“去吃大桌呀?怪不得今天穿了新衣服来上课,快去快去,去晚了可就吃不上了。”我撒腿就往校外跑,父亲正在校门口扶着自行车等我。我参加工作后,马老师陪师母到济南看病,我在单位旁边的一个小饭店请他和师母吃饭,特意点了很多菜,马老师说:“哪里的菜也不如咱老家的大席有味道。”
有一年元旦,三弟结婚,在老家村里举行的婚礼。近水楼台,我又有机会吃了一顿大桌菜,饭菜是请村里的两个焗匠做的,其中一人负责做凉菜,他的一个儿子因病去世不久,那天他负责做的几个凉菜都是苦的,至今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。(全文完)
□贾富彬
2024-11-18 14:28:02
2024-11-18 14:26:07
2024-11-18 14:25:34
2024-11-13 14:35:34
2024-01-26 09:11:53
2023-12-17 10:07:34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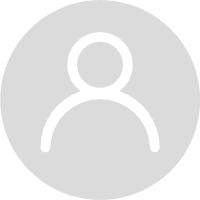
聊城新闻网 2006-2023 版权所有 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/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联合主办
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:37120180030 鲁ICP备09083931号 ![]() 鲁公网安备 37150202000134号
鲁公网安备 37150202000134号
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编号:115330086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(鲁)字第720号
本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:18663509279 举报邮箱:lcxw@lcxw.cn
